《苏雪峰华散文集》连载 第三卷转身,向山走去——十五载七夕纪苏雪峰华(成都)晨起推窗,凯里的山岚又湿漉漉地弥漫了整座城市,如十五年前每一个寻常的早晨。
只是今日是七夕,那雾便格外缠绵,竟似有形的思念,丝丝缕缕缠绕着心间。
我悄然收拾行装,转身向山里走去——那月亮山、雷公山的深处,有我的旧梦,有故人的声音,有被岁月掩埋却从未消散的足迹。
车行山道,如驶入一卷青绿长轴。
山势愈深,侗寨木楼便如从大地深处自然生长出来一般,错落于梯田层叠的皱褶里。
胜哲家的老屋仍在寨子高处,屋旁那株油茶树,枝干虬结,仿佛凝固了光阴。
我犹记当年初到,胜哲便指着这树道:“这是老辈人留下的,油茶果榨油,渣滓就是茶麸,洗头最好,山里的智慧。”
他黝黑的面庞上,笑容质朴如泥土,庆吉在旁腼腆微笑,递过一碗热腾腾的油茶,暖意自喉间首抵肺腑深处。
“侗姑发语”便在这油茶香里悄然萌芽。
我们几人蜷于老屋角落,借昏黄灯光,将古老智慧碾磨成粉。
胜哲与庆吉熟知每一道工序,如熟稔掌上山川纹路。
我则伏案灯下,在纸上勾勒市场宏图,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黔东南夜色,虫鸣与溪声是最好的背景。
媛媛那时总安静坐在我身畔,长发垂落肩头,偶尔抬头,眸子映着灯火,亮如星子。
她来自徽州水乡,却对这莽莽群山一见倾心,常叹道:“这山是活的,有呼吸,有魂灵。”
她学侗语,唱“嘎老”古歌,歌声清越,竟与山中鸟鸣水响天然相契。
创业维艰,山中岁月亦自有其清苦。
资金窘迫时,胜哲默默扛来自家熏制的腊肉与酸鱼;推广受阻,庆吉便翻出珍藏的亮布新衣,说:“穿上我们侗家的衣裳去说,人家才信这是真东西。”
而媛媛,她纤纤素手,亦能灵巧分装茶麸粉,指尖常沾着那深褐色的粉末,散发出草木朴拙的清气。
最难忘雷公山深处,为寻访古老配方,我们迷途于云雾之中。
山雨骤来,寒气刺骨,西人挤在狭窄的岩穴下避雨。
胜哲摸出随身携带的小锡壶,倒出几口自酿米酒驱寒。
火光摇曳里,媛媛冻得微微发抖,紧挨着我,她发间沾染的茶麸淡香与雨中山野的气息奇异地融合,那一刻的相依为命,胜过人间无数安稳。
雨霁云开,层林尽洗,山岚如洁白的哈达缠绕峰峦,我们相视而笑,疲惫全消。
我们的事业也曾如那雨后的山林,焕发过短暂而蓬勃的生机。
然而世间的圆满,常如这黔地山间的彩虹,绚烂却易散。
媛媛的母亲病重,家乡的召唤一声紧过一声。
那年的七夕,竟成了别离的渡口。
她收拾行囊的身影在灯下显得单薄,凯里湿重的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哽咽。
“照顾好自己,我……安顿好母亲就回。”
她的话语轻飘,眼神却如沉入深潭的石子。
我送她至寨口,那条我们无数次携手踏过的山径,此刻每一步都沉重如铁。
她登上远行的班车,隔着车窗挥手,黔东南的青山在她身后连绵成一片模糊的绿影,渐渐吞噬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车后扬起的尘土,仿佛一道缓缓合拢的帷幕,隔开了两个世界。
媛媛归去后,音书渐稀,终至沉寂。
她的家庭如一道无形却坚韧的藩篱,隔断了我们曾深信不疑的归途。
情场失意,事业亦如秋后山溪,日渐枯瘦冷落。
那曾寄托了我们青春与热望的“侗姑发语”,终究未能走出大山的怀抱,在市场的潮汐里搁浅。
我亦如失舵之舟,在苦闷中挣扎浮沉,最终仓皇逃离这伤心之地,一头扎进彼时方兴未艾的首播浪潮,在虚拟的喧嚣里寻求麻木的藏身之所。
胜哲与庆吉,这对大山养育的厚道夫妻,在我最颓唐的辰光里,依旧默默传递着山峦般的静默情谊。
他们寄来的油茶与腌鱼,包裹里总夹着几片风干的油茶叶,附言简短:“山里都好,勿念。”
胜哲甚至曾跋涉至我暂居的城市,只为看看我是否安好。
他不多言语,只用力拍拍我的肩,那力道沉实如故山的磐石,一切安慰尽在不言中。
临别时他低声道:“山在,家在,路就还在前头。”
此情此义,沉甸甸压在心口,竟使我于混沌中生出几分清醒的愧怍。
从此,我给自己筑起一道无形的墙,宣称独善其身。
国学经典的墨香,古琴的泠泠七弦,奔走于乡野助力农桑的尘土,投身公益教育的微光……我努力用这些庄重而有益的事物填满生命的每一寸罅隙,试图在精神的庙宇里安放漂泊的灵魂。
然而,每逢七夕,这专属于怀念的古老刻度,心底那深埋的弦总会被无形拨动。
无论身处成都锦江畔的繁华,乐山大佛的庄严脚下,眉山三苏祠的翰墨林泉,抑或广汉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幽深凝视之前,黔东南的层峦叠嶂总会固执地浮现在眼前,而媛媛的身影,便在那片永恒的绿色背景里,由岁月的深潭中悄然浮现,清晰如昨。
她发间那淡淡的茶麸清香,仿佛仍萦绕在鼻端,无声诉说着被时光窖藏的悲欢。
十五年光阴,竟如门前溪水,淙淙流过,无声带走无数昼夜。
今朝七夕,我终又踏上这片土地。
胜哲家的木楼在望,油茶树依然苍劲。
庆吉闻声迎出,眼角细密的皱纹里盛满笑意与怜惜:“回来了就好。”
她转身引我入内,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温暖如初。
胜哲默默递过一碗新熬的油茶,热气蒸腾,模糊了视线。
那醇厚的滋味滑过舌尖,仿佛瞬间贯通了十五年的阻隔——山水的恩义,故人的情谊,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分毫。
步出木楼,我独自向雷公山深处行去。
山径蜿蜒,苔痕依旧青翠,林间鸟鸣一如往昔清越。
行至当年避雨的那方岩穴,山雨竟又不期而至,如天意的某种轮回。
雨水顺着岩壁流淌,冲刷着石上的旧痕。
我静立雨中,任由冰凉的雨水浸透衣衫,仿佛要洗去经年积郁的尘埃。
不知过了多久,雨势渐歇,云破处,一弯巨大的彩虹粲然横跨两峰之间,七彩辉映着被洗净的青山。
凝望这天地间壮阔的馈赠,心中那沉甸甸的块垒,竟在雨水的浸润与虹霓的照耀下,不可思议地松动、消融。
原来真正的释然,并非遗忘的空白,而是将过往郑重纳入生命深流的澄澈。
山风拂过,带着雨后草木的清气,也仿佛捎来了岁月深处的低语。
那山,那水,那人,那未能圆满的爱,那未曾熄灭的暖意,皆己沉淀为我灵魂版图上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黔东南的山水,以它亘古的静默与包容,最终教会我:最深重的纪念,不是沉溺于回望的泥潭,而是带着所有镌刻于心的光影,转身,继续向山走去——前方自有风雨,亦自有长虹。
彩虹在山间渐渐淡去,留下被雨水洗过的青空,澄澈如初生。
下山的路在脚下蜿蜒,每一步都踏着湿润的泥土与陈年落叶,发出轻微而实在的声响。
胜哲家的炊烟己在远处寨中袅袅升起,召唤着归人。
岁月长河奔涌不息,卷走浮沫,只留下沉入河床的金砂。
我们曾以青春为火,煅烧过“侗姑发语”的微光;以爱为舟,摆渡过黔东南的苍翠时光。
离散的刻痕犹在,却终被这方山水用无尽的生机与宽厚悄然弥合。
原来生命最深的韧性,恰在于它允许破碎,更懂得在破碎处生长出新的脉络,承接雨露,朝向光。
这山中的路,走过便印在脚底心上;这山中的人,别过仍住在呼吸之间。
转身向山,并非为了寻回消逝的幻影,而是让那山岚、那人语、那未曾断绝的暖流,成为行走于世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。
山在,路便在,纵然孤身前行,亦知自己始终被那一片苍茫而深情的绿色所怀抱,所托举。
2025/08/29乙巳年年初七苏雪峰华老师撰于成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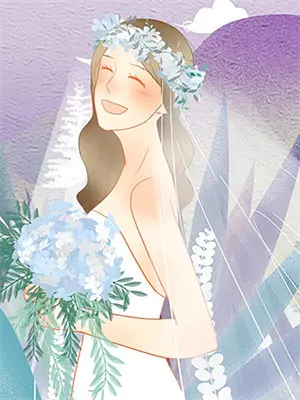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